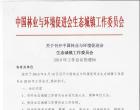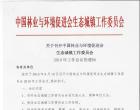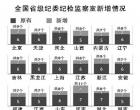新京報制圖/師春雷
近日,教育部網站公布6所部屬高校制定的大學章程草案。這是去年《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》實施后,首批提請教育部核準并公示的高校章程草案。
高校章程被賦予高校“憲法”的地位。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,教育主管部門一直要求高校制定章程,對依法自主辦學、建設現代大學制度,“政校分開、管辦分離”等具有積極意義。
截至目前,除了今年提請核準章程的6所,全國1600多所公辦高校,制定章程的僅有幾十所。又由于在制定章程時,《暫行辦法》未出臺,沒有具體標準,有的章程并不符合現代大學制度要求。
即使是近期公示的6所高校章程,反饋結果也褒貶不一。有專家認為形式意義可能更大;另有專家稱其是“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向前走的一小步”。
2007年啟動,11次大修,2012年定稿。
這是東南大學章程草案,歷經的“磨難”。
“第十一稿與第一稿有天壤之別。”仲偉俊形容6年的艱辛。仲是東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,也是該校章程制定小組的召集人。
2012年,教育部頒布《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》(以下簡稱《辦法》),旨在全面推動高等教育體制改革。有專家解釋,教育部希望更多高校制定合規的大學章程。
直至8月12日,只有東南大學和其他5所部屬高校的草案在網上公示,接受社會“檢閱”。
對于這6部提請教育部核準的章程,不少教育界人士認為,其大同小異,核心問題沒有突破,未擔起“高校去行政化”的使命。
章程現狀
千余高校“無章辦學”
華中師范大學是6所提交章程草案的高校之一。該校教授范先佐認為,無章辦學甚至會讓學校吃官司。
他舉例說,今年年初,重慶工商大學老師集體反對學校的工資改革及績效考核方案(審議稿)。該方案被指對一線教職工存嚴重歧視,而更傾向行政人員。“如果有大學章程,學校就不能隨意出臺損害教師利益的方案。”
要求高校建設章程的內容,最早見于上世紀90年代頒布的《教育法》和《高等教育法》。
2006年6月,教育部開始動員,當時在吉林大學召開“直屬高校依法治校工作經驗交流會”,對大學章程制定工作做了明確要求。
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武漢大學、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都啟動章程制定工作。
但截至2011年,國內1600余所公立高等學校,只有26所高校制定了章程。
武漢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胥青山說,少數制定出的章程,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章程。因為這些章程并沒理清高校內部職能。
2012年,教育部頒布《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》,要求所有公立高校都要建立章程,部屬高校將草案提請教育部核準;地方高校則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門核準。
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曾對媒體表示,《辦法》主要是解決公辦高校多數還沒有章程,或已有章程不符合現代大學制度要求的問題。
同時,教育部還選了26所部屬高校,進行試點,希望其能成為章程建制的示范。
今年7月,26所試點高校中只有6所,向教育部提交了章程草案,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、東南大學、華中師范大學、武漢理工大學、上海外國語大學、東華大學。
其他高校則一直在醞釀。
為何難產
與內部權力博弈有關
除部屬高校在試點,地方高校也在試點章程建設。
2012年1月,湖南有11所省屬高校,被要求用一年時間,完成大學章程建設。到了年底,11所高校中有10所表示不能如期完成。
多所高校稱,制定章程難在“內外部權力界定”。
湖南師范大學是其中一所完不成任務的高校。
該校法律事務辦主任劉興樹說,章程修訂將會改變學校原有的權力結構,內部權力面臨重新洗牌和再分配,這是阻礙章程修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復旦大學高校章程已醞釀3年。
該校校長楊玉良在設計章程時曾提出,將限定包括校長在內各種權力,校領導和部處負責人退出學術委員會和教學指導委員會。章程制定隨后陷入“沉寂”。
東南大學去年提交章程草案。據一名參與制定草案的老師介紹,校領導對章程制定沒有設限,讓放手做,但稿子多次打回來重修。
仲偉俊說,一稿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現有的國內高校管理體制,參照西方高校的管理模式來制定章程,學校自主管理,自主辦學。
“領導看后認為改變太大,不切合實際。”仲偉俊說。
“平衡這些訴求需要藝術。”仲偉俊說,國內大學沒有多少章程可循,“度”很難把握。
教育部出臺《辦法》規定,章程應健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,規范學校黨委集體領導議事規則、決策程序,明確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的制度規范。
“思路明確后就沒有那么難了。”仲偉俊介紹,他們理順章程界限后,采取較穩妥的方式制定出大學章程。
范先佐說,6所學校均有“黨委領導、校長負責、教授治學、民主管理”等字眼,明確了黨委和校長的權力。多數表述中,黨委對重大事項有決策權。但到底學校中什么是重大事項,沒有明確界定,現實操作并不好把握。
章程瓶頸
“去行政化”的現實差距
高校自制章程,是否意味著就能去“行政化”?有專家對此不樂觀。
6所高校章程中,兩所高校章程明確指出,校長由舉辦者任命。而有教育專家認為,校長任命制正是大學“行政化”和校長“官員化”的重要原因。
“行政化”首先要厘清學校和舉辦者間的關系。
《辦法》明確規定“舉辦者、教育行政部門應按照政校分開、管辦分離的原則……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權”。
武漢理工大學等4所大學在涉及“外部關系”的某一章節中表述了這些內容。
東南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則在“舉辦者與學校”、“學校的舉辦者”中對相關內容進行了清晰表述。
其中,東南大學章程規定“學校舉辦者”的權利和義務共達13項,包括“舉辦者不得在法律、行政法規無明文規定的情形下任意限制學校辦學自主權”、“舉辦者應保障學校的辦學條件”等。
上述教育界人士指出,有了這些條款,教育主管部門將不得橫加干涉學校設置專業、選聘教授等自主權。
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秦前紅認為,章程形式意義多于實質意義,“今后有可能章程擺到一邊,不照章去做”。
作為該校參與制定章程的一線教師,秦前紅說,目前大學確定招生數量、形式,考試辦法等,都是行政行為,大學自己說了不算,“總的束縛就是高校體制”。
現實意義
有總比沒有好?
胥青山和秦前紅同為武漢大學教授,胥青山則有不同看法::“有一定比沒有好。”部分高校試點制定章程,是“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向前走的一小步”。
在現有6所高校的章程里,能找到自主辦學的相關內容,如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東南大學的章程里,規定了自主調節系科招生比例。
防止“學校吃官司”,對教職工的管理方面,中國人民大學的章程要求比較具體。該校規定教職工享有“就職務聘用、福利待遇、評優評獎、紀律處分等事項表達異議和提出申訴”等權利,但在應履行義務條款中規定,“未經學校批準,不得在校外兼任實職”。
一些美劇里,有時可看到這樣的情景:大學生觸犯了校規,但并沒立刻受到處罰,而是首先要面對類似仲裁委員會的組織,進行陳述、申訴等。
6校在各自章程里,也對學生享有的權利進行了明確。比如東南大學規定學校建立學生聽證、申訴等權利保護機制。
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表示,高校是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組織屬性的法人組織,這批章程中均強調了高校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法人主體。目前我國還沒有學校法人的概念,高校作為獨立法人,應具有哪些法人權利,形成什么樣的法人治理都還在逐步探索中。
秦前紅認為,章程對大學內部能起到約束作用。比如評教授、評職稱的權力如何分配。
“但如果超越內部范圍,輻射到外部去了,可能就無能為力了。”
新京報記者 涂重航 實習生 賈世煜 北京報道
(新京報記者郭少峰對此文亦有貢獻)
(原標題:高校章程“難產”:上千所只6所提交)